Relationship among oil and gas resources, reserves and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ational oil and gas resource assessment
-
摘要: 为了加深对资源量、储量、产量三者的内涵和实质关联的正确理解,从理论逻辑和实际转化两个角度对三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剖析和阐述,并结合应用现状分析,提出了资源评价方面发展方向建议。资源量、储量、产量是不同认识程度下的油气矿产资源的数量表征参数,我国的储量与资源量呈并列关系,与产量呈包含关系,资源量与储量均为地质含义。资源量向储量转化受国家空间规划、矿业权设置、理论技术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储量向产量转化受储量升级转化、是否转采、采收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资源量评估与发布的侧重方向,以及资源量、储量、产量量化预测关系等方面研究尚不足,这也是形成“我国资源潜力丰富,但增储上产难度大”资源现状认知困惑的重要原因。资源评价内容及结果应用分析的丰富和发展,有助于形成对油气资源现状的全面深入的认识。应从对评价结果进行可动性分级、加强(待发现)可采资源量评价、强化成果应用分析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发展。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and substantive relationship among oil and gas resources, reserves and production on a deeper level, this paper made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elabo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resente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esource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status. Resources, reserves and production are estimated quantities of oil and gas mineral resources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understanding. In China's classification system, reserves and resources are in a parallel relationship, and reserves and production are in an inclusive relationship. Both resources and reserves are geological meaning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esources to reserves is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mining right setting, theoretic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eserves to production is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reserves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whether to convert to mining, recovery factor, etc. China still has some deficiencies in resource assessment and release, as well as quantitative prediction of resources, reserves and production,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cognitive confusion of "China has rich resource potential but it is difficult to increase reserves and production".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 assessment contents and results application analysis will help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It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from the following respects: mobility classification of assessment results, assessment of (undiscovered) recoverable resources and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results.
-
Key words:
- oil and gas production /
- oil and gas reserves /
- oil and gas resources /
- resources assessment /
- China
-
油气的资源量、储量、产量是石油工业上游最基本的参数,构成了一套复杂的术语系列,用于定量表征石油行业勘探开发现状,在行业形势研判和发展规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国内外不同机构对三者提出了诸多版本的术语定义[3-10],使得目前在社会甚至油气、能源业界等的应用中仍存在许多混淆和误解。尤其是近年来,“我国资源潜力丰富但增储上产难度大、国家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现状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对我国资源现状认知的困惑,现有的分析多从我国资源储量的品质、禀赋等角度对此矛盾现状进行分析解释,尚缺乏从资源量—储量—产量关系角度的剖析和阐述。2020年5月,自然资源部颁布实施新的《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9492—2020》标准(本文简称国标2020)[7],对资源量、储量等术语系列的分类和定义做了修订。本文在新标准、新形势背景下,对资源量、储量、产量系列术语及三者之间关系做出系统深入的分析,并基于资源储量评价方面的应用现状分析,提出我国油气资源评价未来发展方向,以期实现对油气矿产资源现状的全方位、多角度的正确认识。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应用中,产量包括年产量、单井日产、累计产量等不同含义,文中产量系指在某一时间之前累计产出的油气的量,即累计产量。
1. 资源量—储量—产量的理论逻辑关系
不同国家或机构等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需求建立了多种资源储量分类方案,截至目前已有十余种[3-6]。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分类体系主要包括PRMS(2018版)[8]、俄罗斯(2016版)[9]、挪威NPD(2016版)[10]、美国USGS(1995版)[3-5, 11]和我国国标2020版(GBT19492—2020)等[11]。分类体系的术语可分为资源量系列、储量系列和产量三大类,其中资源量系列和储量系列又根据具体含义分为地质系列和可采系列。资源量、储量、产量三者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可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1.1 资源量、储量、产量内涵
(1) 资源量、储量、产量是不同认识程度下的油气矿产资源的数量表征参数。油气矿产资源深藏地下、隐蔽性强、探测识别难度大,其流体性质决定了在地下分布的复杂性和规模的不确定性。由于勘查开采工作的不均匀分布,导致对地下矿藏的了解程度有粗有细,资源量、储量、产量即是不同认识程度下油气矿产资源的数量表征参数[11]。资源量(Resources)是发现石油之前估算的油气数量,可靠性程度通常较低;储量(Reserves)是发现石油之后估算的油气数量,具体再基于不同圈闭或区块的地质认识程度或工业开发程度差异具有不同的可靠程度,比如,我国的探明、控制、预测地质储量的可靠性程度逐渐降低;产量(Production)则是真实产出的、确定的油气数量,可靠性程度为100%。
(2) 我国资源量与储量均为地质含义,而非可采含义。资源量和储量通常分别为分类体系中资源量系列和储量系列术语的统称。对于国外分类体系而言,资源量通常指未发现原地油气聚集中潜在可开采的油气估算量,具有可采含义。储量内涵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已发现原地油气聚集中可采部分的估算量,比如俄罗斯(2016版)、美国USGS(1995版);二是已发现原地油气中具有商业性或经济性可采部分的估算量,比如PRMS(2018版)、挪威NPD(2016版)。我国分类体系中储量则通常指已发现原地油气聚集的估算量,为地质含义,包括可采部分和不可采部分;资源量通常包括已发现和未发现的总原地油气的估算量,如国标2004,或者未发现原地油气的估算量,如国标2020,均为地质含义。
1.2 逻辑从属关系
各分类体系的分类基础大致相同,均是总原地油气(即地下蕴藏的油气聚集)的估算量。PRMS(2018)中将其称为总原地油气量(Total Petroleum Initially-In-Place,即PIIP),共分为产量、储量、条件资源量(或储量)、已发现不可采部分、远景资源量、未发现不可采部分6个部分;俄罗斯(2016版)、挪威NPD(2016版)、美国USGS(1995版)等国外体系大致相似。国标2004体系中称为总原地资源量,分为地质储量(又称已发现原地资源量)和未发现原地资源量2个部分,产量是地质储量中经济可采系列的一部分[12];国标2020中将自然聚集物的数量进一步分为资源量和地质储量两类,产量是地质储量中经济可采系列的一部分(图 1)。
由此可知,国外的分类体系中,资源量、储量、产量呈并列关系;国标2004中,三者呈包含关系;国标2020中,资源量与储量的关系调整为并列关系,储量与产量的关系仍为包含关系。
2. 资源量—储量—产量的实际转化关系
2.1 资源量与储量的转化
资源量向储量的转化是发现油气的过程,主要通过勘探工作实现,但受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资源量并非100%转化为储量。
(1) 平面上,受国家整体空间规划及相关政策等的影响,形成一定范围的勘查开采禁止区、城市规划区、军事禁区等,压覆一定数量的油气矿产资源(图 2a的Ⅰ环节)。根据我国“三区三线”等空间规划政策以及建设需要,矿业权设置时需要避让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林地、草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二是勘查开采禁止限制范围,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国家级勘查开采禁止限制范围,省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水源地、军事禁区等;三是应避让的重要工程设施范围,如港口、机场、国防工程设施圈定地区,重要工业区、大型水利工程设施、城镇市政工程设施附近一定距离范围内,铁路、重要公路两侧一定距离以内,重要河流、堤坝两侧一定距离以内等[13]。因此,由于国家整体空间规划及相关政策等的影响,导致一定数量的资源量被压覆,暂时无法向储量转化。
(2) 未设矿权区或已设矿权区内未开展勘探的区域,存在一定量的待释放油气矿产资源(图 2a的Ⅱ、Ⅲ环节)。一方面,我国尚有一定范围的地区未设立矿权,这些地区中蕴藏着可观数量的资源潜力。为此,2020年我国颁布了《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自然资规〔2019〕7号,简称“7号文”),提出了继续推进油气探矿权竞争性出让试点的举措,是推动释放这部分油气矿产资源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对于已设矿权的区域,受油气地质条件差异、勘探成本等的影响,勘探工作通常遵循“先易后难”、“先优后劣”的规律,优先勘探开采在平面上的局部有利地区(或区带)和纵向上局部深度、层系范围内的油气,在矿权区域内仍有相当数量的勘探面积尚未开展勘探工作,使得该面积内的油气资源量未释放。自然资源部“7号文”中提出了“调整探矿权期限”“开放油气勘查开采市场”等意见,可以有效推动释放该部分资源。
(3) 已开展勘探工作的地区,受地质、理论、技术等因素限制,存在一批尚未涉及领域的油气矿产资源(图 2a的Ⅳ环节)。随着有利勘探区勘探程度的不断加深,勘探工作会逐步向难发现、劣质化资源推进。受油气勘探理论认识阶段性发展、勘探开发技术局限性等的限制,平面上已开展勘探工作的地区也仍有某些领域的资源无法发现,比如当前尚有待理论技术进一步突破的天然气水合物、页岩油、深层、深水等领域,或是受圈闭识别技术局限的限制,大量无法被识别的小规模、复杂隐蔽油气藏等,均导致这部分资源量目前无法实现向储量的有效转化。
(4) 已开展勘探工作的地区,受成本或经济条件因素等限制,一定数量的资源尚未经钻井验证(图 2a的Ⅳ环节)。已开展工作的地区,除了理论、技术等因素限制无法涉及的领域外,还有部分区域,虽然理论和技术条件满足,且已经开展了相对详实可靠的勘探研究工作,但考虑到钻探成本、经济条件或勘探风险等因素,目前无法达到经济可行性的标准,一直未经钻井验证。
综上可知,通常只有非勘探禁止区内、已设矿权区域、理论技术经济条件均满足的区域,才可能会逐步开展钻井验证,并在一定勘探成功率的限制下,实现由资源量转化为储量。
2.2 储量与产量的转化
勘探钻遇或预测有油气层后,资源量便可升级为储量。按国家储量管理相关要求,当井控程度和试井产量等达不到探明储量标准时,通常先升级为预测储量或控制储量。储量向产量的转化是已发现油气采出的过程,主要通过评价勘探和开发工作实现,但受以下几方面的限制,储量并非100%转化为产量。
(1) 部分控制储量和预测储量等未成功升级为探明储量(图 2b的Ⅴ环节)。控制储量和预测储量由于地质可靠程度较低,通常需要继续开展评价勘探,并达到探明地质储量的勘探开发程度和地质认识要求,才能升级为探明储量作为下一步转为开发阶段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其中,根据我国储量估算规范[14],只有含油(气)范围的单井稳定日产量达到储量起算标准,即油(气)藏不同埋藏深度下油气的单井日产量下限(最低经济条件),这部分油气量才能升级并纳入探明地质储量范畴。剩余未达到储量计算标准的油气储量则无法升级为探明地质储量,亦无法开展下一步开发部署向产量转化。
(2) 技术和经济等原因导致部分探明地质储量尚未转采,存在探明未开发储量“库存”问题(图 2b的Ⅵ环节)。已探明地质储量中,有部分储量因“品位差、丰度低、开采成本高、开发难度大”而长期搁置,这类储量通常经产能建设的严格筛选后,具有“油层薄、物性差、埋藏深、投资大、成本高”等共性。据统计,截至2017年,东部主力油田的探明未动用石油储量占探明总储量的比例平均为21.6%[15]。
(3) 已开发的探明地质储量受采收率等因素限制与最终累积产量有一定比例的折扣(图 2b的Ⅶ环节)。受油气藏(田)地质条件和现有开发采油采气工艺水平等限制,导致探明地质储量中只有部分的油气被采出,而剩余一定数量的油气会滞留在地下无法开采出来。储、产量报告数据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各产油气盆地石油采收率为5%~38.9%,平均值为21.8%,天然气采收率为24.1%~ 88.0%,平均值为53.1%,且历年来油气的采收率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资源劣质化而开采技术尚未突破导致。
(4) 与探矿权一致,采矿权的设置同样受国家整体空间规划及相关政策等的限制,压覆了一定的储量、产量油气矿产资源。近年来,在我国“三区三线”等政策下,陆域油气矿业权范围内受生态环境保护影响,已关停一定数量的油井、气井,海域生态环境保护、军事区等与油气矿业权重叠区内也压覆了一定数量的储量和产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据不完全统计,上述因素导致陆域和海域压覆石油、天然气年产量不足全国年产量的1%。
3. 应用现状分析
综上可知,一方面,资源量、储量、产量分别是未发现、已发现、已产出等不同认识程度下油气的数量表征参数,通常基于相对独立的评估、统计工作获得。另一方面,资源量、储量、产量三者之间受政策(或管理)、理论技术、经济等因素影响,在勘探开发实际中为逐级转化关系,存在发现概率和开采概率(图 3),可以通过量化不同因素影响量实现资源量与储量、产量之间,以及储量与产量之间的预测关系。要想实现社会对油气资源量、储量、产量的正确认知,达到应用效益的最大化,除了从理论逻辑和实际转化关系上客观、定性地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实现对不同类型和级别油气资源储量的准确评估,以及资源、储量、产量三者之间的量化预测。
我国的油气储量评估工作通常由油公司评估,政府部门审核,具体包括地质储量评估、技术可采储量评估、经济可采储量评估等。一般而言,地质储量为已发现目标总的原地油气量,技术可采储量为仅扣除技术因素影响后预计累计可采出的数量;经济可采储量为扣除技术、经济因素影响后预计累计可采出的数量,近似理解为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的预计累计总产量,它与地质储量的比值可定义为开发概率;剩余经济可采储量可近似理解为预计剩余累计产量,年度储产量报告中通常以储采比(即年末剩余探明经济可采储量与年产量的比值)表征当前生产水平下油气尚可供开采的年限。因此,基本实现了各级储量的准确评估,以及储量向产量转化过程中各类因素折扣量的量化预测。
国标2020颁布之前,全国油气资源评价在国标2004的框架下开展,评价内容具体包括地质资源量(即总的原地油气量)评价、可采资源量评价、经济可采资源量评价等,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油气资源评价工作通常侧重估算并对外公布总的原地油气量,包含已发现和未发现、可采和不可采在内的所有油气的量,数值通常较大,无法直观反映资源潜力,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认知成本,且常被社会错误地理解为目前尚未发现、潜在可采出的油气的量,从而形成了可观的资源量评估结果与我国油气产量不足、能源安全形势紧迫的实际现状的主观矛盾。比如,我国石油的地质资源量超千亿吨,年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只有十几亿吨,年产量仅约二亿吨,据初步统计,地质资源量(包含已发现和未发现,含常规油、致密油、页岩油)、累计地质储量(含探明地质储量、控制地质储量、预测地质储量)、累计产量三者之间比例约为20∶8∶1,这些数值差异形成了“资源量偏大”、“过于乐观”等主观上的误解,甚至对资源评价的意义和用处产生质疑。二是可采资源量(即潜在可技术采出的油气的量)的计算通常由地质资源量乘以可采系数获得,可采系数多是以成熟探区采收率为基础数据构建定量模型或直接类比获得,相当于是评价区预计采收率,而采收率通常是储量向产量转化过程中开发概率的定量表征参数;实际上,由资源量推测潜在可采出的量需要考虑发现概率和开发概率两个要素(图 3b)。因此,评价所得的可采资源量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经济可采资源量评价,分别相当于假定发现概率为100%的条件下,预计可技术采出和可经济采出的油气的量,与实际勘探不符、且尚未实现资源量向储量转化过程中各类控制因素的影响量估算,以及资源量与储量、产量量化关系的预测。
国标2020分类标准颁布之后,对资源量系列进行了调整,将资源量内涵调整为扣除已发现的原地油气量(即地质储量)之外的待发现的原地油气量,从理论逻辑关系和内涵的基本点上,将资源量与储量调整为并列关系,进一步减小了资源量、储量、产量数值差异,如前所述的我国石油资源量、累计地质储量、累计产量三者的比例关系约为12∶8∶1,使得资源量更加直观地反映我国剩余油气资源勘探潜力,可以有效地降低社会认知成本,也是形成对油气资源现状正确认识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针对待发现的油气中预计技术可采量、预计经济可采量的评价,以及资源量、储量、产量三者之间影响因素及相关关系的量化预测,仍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4. 我国油气资源评价发展方向
综上可知,为了实现社会对资源量、储量、产量的系统、准确认知,还应当在国标2020分类标准框架下,进一步丰富全国油气资源评价工作内容,加强评价结果综合分析,提升资源量—储量—产量三者之间的关联性。综合考虑资源量—储量—产量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转化关系以及应用现状分析,拟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方向可供参考。
一是丰富(待发现)资源量政策可动性评价。资源量向储量转化过程中,第一个扣除环节是国家空间规划等导致的无法设置矿业权的地区对油气矿产资源的压覆。“十三五”全国油气资源评价初次探索了这部分资源的量化评价,创新性提出油气资源生态评价工作方案,可以获得生态红线内、外的资源分布情况。未来也将探索实现对林地、草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等国家级勘查开采禁止限制范围、军事禁区、城市规划区等不同规划用途类型、无法设置矿业权的区域内的压覆资源量评价,获得评价周期内可供勘探的资源量。
二是加强(待发现)可采资源量评价。地质含义的资源量属于“确定性”静态参数,适用于中长期规划管理用途,而可采含义的资源量受某一时间点(或段)技术工艺和经济条件控制,属于“不确定性”动态参数,适用于短期规划和实时资产管理,两者各有优势。虽然新的油气资源储量分类标准(国标2020)中未对资源量进行可采性的分类分级,但就资源评价工作而言,仍然建议在地质含义的资源量评价的基础上,加强可采资源量(包括技术可采和经济可采等)的评价,创新或改进评价方法,做到发现概率和开采概率的兼顾。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国外分类体系中资源量均为待发现、可采含义,加强(待发现)可采资源量的评价,可以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增加可比性和国际话语权;二是有利于量化当下理论、技术、经济条件下,导致无法发现的量(图 2a环节Ⅳ)以及发现后不可采出的量(图 2b环节Ⅶ)等,掌握更为实际、客观的资源潜力。
三是强化结果应用性综合分析。新形势下,油气资源评价的最终目的除了最基本的“摸清油气资源家底、分布、品质情况等,服务于国家规划和油田企业勘探部署”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研究的重要依据。加强资源评价结果应用性综合分析,根据资源量—储量—产量实际转化关系,探索不同环节的定量化评价模型,一方面可以量化不同环节、不同因素影响下资源的折扣数量,为国家规划和油气能源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以求有的放矢、制定相应的各项政策和管理措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另一方面可以最终获得(待发现)资源量预计可转化的累计储量,以及进一步可转化的预计累计产量,并结合已发现储量、产量情况综合分析,从用的角度回答是否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到什么程度等,也是从“结果导向”的角度破解资源评价意义质疑的重要思路。
5. 结论
(1) 理论上,我国资源量系列与储量系列呈并列关系。资源量是发现油气之前的估算量,储量是发现油气之后的估算量,产量是储量中已被采出的部分,三者确定程度不断增加;油气资源量和储量的分类基础均为包含可采和不可采部分在内的地质含义,可根据技术可采和经济可采性进一步分类分级。
(2) 实际上,资源量、储量、产量呈逐级转化关系。资源量向储量转化是油气发现的过程,受政策、理论技术、经济等因素影响,只有政策允许范围内且具有理论技术、经济可行性的油气资源可以被成功勘探发现,转化为储量;储量向产量转化是油气开采的过程,受技术、经济等因素影响,只有具有经济开采性的油气储量可以被成功开采出来,转化为产量。
(3) 资源量的地质含义属性及向储量、产量转化中的影响因素,是形成“我国资源潜力丰富但增储上产难度大、国家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现状的根本原因。丰富资源评价内容,探索实现各类因素影响的量化预测及不同类型、级别资源储量的准确评估,打通资源量—储量—产量定量关系通道,是推动油气能源安全保障研究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国家空间规划等政策因素对评价结果进行可动性分级,加强发现概率和开采概率兼顾的(待发现)可采资源量评价,强化成果应用性综合分析等研究,是全国油气资源评价未来发展的方向。
-
-
[1] 张抗, 卢泉杰. 油气资源量—储量—产量系列词语辨析及其他[J]. 石油科技论坛, 2015, 34(3): 61-67. doi: 10.3969/j.issn.1002-302x.2015.03.013ZHANG Kang, LU Quanjie. Clar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petroleum resources-reserves-production term series[J]. Petroleu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um, 2015, 34(3): 61-67. doi: 10.3969/j.issn.1002-302x.2015.03.013 [2] 万吉业. 石油天然气"资源量—储量—产量"的控制预测与评价系统[J]. 石油学报, 1994, 15(3): 51-60. doi: 10.3321/j.issn:0253-2697.1994.03.001WAN Jiye. Controlled prediction and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oil and gas "resource-reserve-production"[J]. Acta Petrolei Sinica, 1994, 15(3): 51-60. doi: 10.3321/j.issn:0253-2697.1994.03.001 [3] 查全衡. 国内外油气资源分类沿革及启示[J]. 石油科技论坛, 2020, 39(4): 7-15. doi: 10.3969/j.issn.1002-302x.2020.04.002ZHA Quanheng.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oil and gas resources classification[J]. Petroleu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um, 2020, 39(4): 7-15. doi: 10.3969/j.issn.1002-302x.2020.04.002 [4] 康永尚, 刁顺, 陈安霞, 等. 中外油气资源分类体系对比和资源潜力概念探讨[J]. 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 2013, 35(1): 66-7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AGX201301011.htmKANG Yongshang, DIAO Shun, CHEN Anxia, et al. Comparis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etroleum resourc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nd discussion on resource potential concepts[J].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35(1): 66-7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AGX201301011.htm [5] 查全衡. 代表性石油资源分类的比较研究[J]. 石油学报, 2008, 29(6): 809-814. doi: 10.3321/j.issn:0253-2697.2008.06.004ZHA Quanheng.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ypical classification of petroleum resources[J]. Acta Petrolei Sinica, 2008, 29(6): 809-814. doi: 10.3321/j.issn:0253-2697.2008.06.004 [6] 张伦友. 国内外油气储量的概念对比与剖析[J]. 天然气工业, 2005, 25(2): 186-189. doi: 10.3321/j.issn:1000-0976.2005.02.059ZHANG Lunyou.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oil/gas reserve concepts[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05, 25(2): 186-189. doi: 10.3321/j.issn:1000-0976.2005.02.059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9492-2020[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20.State Administration of Market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lassifications for petroleum resources and reserves: GB/T 19492-2020[S]. Beijing: Standards Press of China, 2020. [8] SPE, WPC, AAPG, et al. Petroleum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2018 update (Version 1.01)[M]. [S. l. ]: SPE, 2018. [9] 张建国, 史建忠, 王世艳. 2016版俄罗斯储量-资源量规范与石油工程师协会SPE-PRMS对比研究[J]. 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 2017, 37(13): 140-14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GBJ201713067.htmZHANG Jianguo, SHI Jianzhong, WANG Shiyan.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2016 Russian reserve resource specification and SPE-PRMS of the 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J]. China Petroleum and Chemical Standard and Quality, 2017, 37(13): 140-14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GBJ201713067.htm [10] KNUDSEN K R. The Norwegian Petroleum Directorate's resource classification system[J]. Norwegian Petroleum Society Special Publications, 1996, 6(7): 77-8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8893707800099 [11] 胡洪瑾, 姜文利, 李登华, 等. 油气资源储量分类体系对比及中国最新分类体系特点[J].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2022, 43(3): 724-73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YYT202203021.htmHU Hongjin, JIANG Wenli, LI Denghua, et al. Comparison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reserves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test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a[J]. Oil & Gas Geology, 2022, 43(3): 724-73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YYT202203021.htm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分类: GB/T 19492-2004[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4.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lassifications for petroleum resources/reserves: GB/T 19492-2004[S]. Beijing: Standards Press of China, 2004. [13] 韩亚琴, 景东升, 司芗, 等. 浅析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环境影响评价与矿业权管理[J]. 中国矿业, 2021, 30(4): 15-1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KA202104004.htmHAN Yaqin, JING Dongsheng, SI Xiang, et al.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mining rights management[J]. China Mining Magazine, 2021, 30(4): 15-1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KA202104004.htm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石油天然气储量估算规范: DZ/T 0217-2020[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20.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ulation of petroleum reserves estimation: DZ/T 0217-2020[S]. Beijing: Standards Press of China, 2020. [15] 刘斌. 探明未动用石油储量有效开发的对策探讨[J]. 中国矿业, 2019, 28(3): 40-4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KA201903008.htmLIU Bin. Discussion on the countermeasure of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unused oil reserves[J]. China Mining Magazine, 2019, 28(3): 40-4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KA201903008.htm 期刊类型引用(3)
1. 肖红,钱祎鸣. 基于CNN-SVM和集成学习的固井质量评价方法. 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 2024(04): 960-970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2. 李小冬,郑伟,史原鹏,马学峰,王元杰,田建章,李奔,罗金洋,姜福杰. 基于全油气系统理论的油气资源评价方法——以冀中坳陷武清凹陷沙河街组三段为例. 断块油气田. 2024(05): 778-785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3. 梁君宇,李斌,周立国. 矿产资源评估中不确定性量化方法的研究. 世界有色金属. 2024(18): 226-228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其他类型引用(4)
-






 下载:
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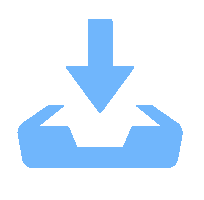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苏公网安备32021102000780号
苏公网安备32021102000780号